大承气汤
大黄四两,用酒洗,厚朴半斤炙去皮,枳实五枚炙,芒硝三合。以上四味药,用水一斗,先加入厚朴、枳实煎煮至五升,去掉药渣,再加入大黄,煎煮成二升,去掉药渣,加入芒硝,然后放在小火上煮一、二开,分两次温服。服药后如果大便已通,停止再服剩余的药。
方剂介绍
【症状】(阳明病)脉迟,身上出汗,不恶寒,身重,短气,腹满而喘,蒸蒸发热,手足微汗。
【组成】大黄四两,用酒洗;厚朴半斤炙去皮;枳实五枚炙;芒硝三合
【用法】以上四味药,用水一斗,先加入厚朴、枳实煎煮至五升,去掉药渣,再加入大黄,煎煮成二升,去掉药渣,加入芒硝,然后放在小火上煮一、二开,分两次温服。服药后如果大便已通,停止再服剩余的药
【胡希恕】“阳明病,脉迟,虽汗出不恶寒者”,这是阳明病的外证俱备,“阳明病,汗出、不恶寒、但恶热”。那么虽然见其汗出而不恶寒,阳明病的外证已备了。但是,由于脉迟的关系,里头不会结热太甚的。
“其身必重,短气”,其身必重者就是外有湿。湿在人的组织里面,人身上就沉。“短气”是内有饮,这是《金匮要略》上的,病人“凡食少饮多,水停心下。甚者则悸,微者短气”。甚者则悸,厉害的时候,心跳,咱们说水气凌心,(这是)古人那个术语。微者短气,轻的话,停水少,也悸。短气还是里有微饮,胃还是有停微饮。
“腹满而喘”,既然是停饮,里边的结实当然不是那么实。腹满而喘”(前面曾讲过讲过)实证类型:如果里头实的厉害,往上压迫横膈膜也喘、也满;那么(本条)这个“腹满而喘”,是热往上壅之象。胃既有停饮,同时热再再壅,那么这两项结起来,也能使着腹满而喘。那么言外之意,在这个情形之下“不可下也”。
所以古人文章净要笔管(讲求文字)嘛!一个“虽”字,这个“虽”字是个否定口气。
“虽汗出,不恶寒者,其身必重,短气,腹满而喘。”那么这个情况,全是不可下的证候。
到这块儿是一句(一个段落)。他暗示,假设阳明病脉迟恐怕其虚。要有这些证候的话,没实到家。我们前面讲了“系在太阴”(第187条、第278条)嘛,病传于里,就是胃肠之里,这个时候假设这人素日里头多湿多饮,就是里头有水,如果湿胜过热,邪热传里头去了,那么就要发生太阴病。太阴病就腹痛、下利;如果热要是胜湿,阳明病法多汗,水火两个东西不同时存在的。如果热盛了,它伤人津液,一方面出汗,方面小便数。(如果)体外没有什么津液了,身子不会沉的。沉(其身必重),说明还有很多湿。所以这个时候,里头不会那么样子实的,热结不会那么甚的,那么这个情形不可下也。
“有潮热者”,这个“潮热”并不是“日晡所”那个时候发热。这个(有潮热)也有人给解释错了,认为“潮”是主“信”,到时候发热叫“潮热”,(我认为)这错的。(本条)这个“潮”就说明来势汹涌这种热,就是热之甚也。我们常打比方,小说上也常有(比方),说兵马齐来如潮水一般,就是言其势又众又多。阳明病这个热就是潮热,蒸蒸发热嘛。如果有这种的热(蒸蒸发热),正说明“外已解,可攻里也”,这个时候可以议下。
但是议下,这在原则上讲可以下,但是还不一定。如果“手足溅然汗出者”,阳明病法多汗,身上早就出汗了,手足也不断出汗,绵绵有汗,这是大便已硬之候,大便都燥结了。
“大承气汤主之”,这才能用大承气汤。大承气汤这个方药泻下猛峻,那要慎重用,必须有潮热,而大便也硬。那么大便硬有多种证候。“手足然汗出”这也是大便硬的一种证候。大便在里头,外证上的反映“手足然汗出”。就像我们方才所说,阳明病是热盛,使着津液尽量往外走,里边不但不能有水了,而且也确实干了。
(金匮要略方注)这一段好得很。“心下坚”是个实证,准拒按。其脉平,“三部脉皆平下利的脉一般说呢,要是没有心下坚,脉平,问题不大。心下坚而脉平,肯定是实。那么为什么“急下之”呢?这与吴又可《瘟疫论》是一样的。这个“下”不能再结实了。
胃这个地方坚,它结实了,说明这个病了不起啊:一方面下,一方面结结者自结,下者自下。一方面泻肚,一方面胃里头凝固起来了,结实了,就是“胃家实”这种反应来了。这说明这个病来得相当猛,不加以急治,危险得很。所以我们治病,这个病最容易给人耽误。“心下坚”,不只是心下坚,也疼,拿手按它,更拒按。
不是咱们现在说,大承气汤治痢疾,这是糟践人,你得辨证啊,这是一种(下利)。其脉平,心下坚,坚且痛,急下之,宜大承气汤。下利不应该结实,吴又可说是瘟疫,这个病厉害。这是边下、边结,一方面下、一方面结。这样则津液也快丧失,结实也太厉害。如果津液丧失到家了(殆尽),人虚下来了,那结实就没办法(治疗)了,大承气汤没法用,那就坏了。所以病实人虚,下之也得死,不下更得死,这就把人耽误了,所以他搁个“急下”。
还有,从脉上来看。“脉迟”,在《伤寒论》里也有这么一段。脉迟,本来是个不及的脉,是为虚为寒,上边不是有“脉沉而迟”(下利,脉沉而迟,其人面少赤,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)吗?
“脉沉而滑者”,脉迟与滑同时见,这个“迟”说明正是实,实到相当程度,它阻碍气机,脉不流畅,不那么快了,迟而滑,这是实。不可轻视,利不是要止的样子,“急下之,宜大承气汤”。
这一段(脉反滑)与上面那一段(脉迟而滑)就差一个迟,脉也滑。“下利”,脉不应该滑,“反滑者”是里头实。“当有所去,下乃愈”,一攻就好'宜大承气汤”。
为什么不说急下呢?它只是脉滑,还没到脉迟的程度,脉迟说明正有欲虚的表现,那你再给延误,就不行了。那个(脉迟而滑,急下之)实得比这个脉反滑)厉害,里头这个实已经阻碍气机了,所以脉也不那么流畅了,这得急下。
底下这段(脉反滑者,当有所去,下乃愈,宜大承气汤)虽然滑,但是没有那种情况,也得下,但不是那么急。所以张仲景的辨证是极有分寸的。旁人在这里头搞(整理编撰仲景遗著),搁的东西都那样(所增与附方值得我们高度警惕,恐非仲景之意),你看头一章脏腑经络先后病,那个文章与他(张仲景)这个不一样,就是论脉论证也不一样,所以那一看就知道不是他(张仲景)的。五脏风寒积聚篇里头也有很多不是他的东西。所以这个书经过王叔和收集、整理一番,大概后来又散失了,不像《伤寒论》那样比较完整一些。这里后人附的东西也不少。这几段说得相当好。
这是说休息痢了,下利本来已经好了,那么到某年某月某时,它又复发了.这就是病毒没尽的关系,那非攻不可。这种事情也是常见的。咱们在临床上,遇到痢疾,一般都喜欢用乌梅这类酸敛东西,常常一开始就用这种收敛药。那么,利也好了,但是不久又反复了,这也是说明休息痢的一种。尤其热痢的开始,据我的观察没有补法,补法很少啊!都是该攻不攻,把病毒遗留到里头了,早晚都是祸。就是痢疾不再发,也能为其他的祸患。这段就是啊。
他说“下利已瘥”,里头很含蓄,也有自己没治,患者他也就(自己)好了。再不,自己吃些烧鸡蛋之类,这都是一种补法,当时也好了。但是不久又复发。复发之后,要是不泻,一半时病也不好,这个依法当下,宜大承气汤。
大承气汤我们也不必太迷信,不必非大承气汤不可,我们要看情形了。如果恶心、胸胁满,那大柴胡汤就行。那么要是即或没有柴胡证,(用)调胃承气汤啊,最常用的药之一,也有大黄、芒硝,但是没有厚朴、枳实,它不那么大胀大满。如果胀满得厉害,大承气汤是非用不可的;不那么胀满,用调胃承气汤就行。我们不一定非得用大承气汤不可,但真正大实大满还得用的。
这个书的证候总是不全,因为在《伤寒论》里头都有,所以在这儿就随便一说,休息痢当下,也是说用大承气汤(这是随便一说啊)。大承气汤证当然是大承气汤,没有大承气汤证,下之就可以的(不一定非得大承气汤),就是随证而施了。大承气汤方在痉病里头,咱们已经讲了。
(金匮要略加注)产后七八天的时候,没有表证,“无太阳证”,不是(所谓)产后受风的问题,“少腹坚痛”,这是瘀血的地方了,少腹这个地方按着硬而且痛得厉害“此恶露不尽”,这(句话说得对)没有问题。妇人产后血液、恶露不是正常的血,只要去净就好了,这是恶露,去而没尽,集成一种坚块在少腹的地方,又坚又痛。
那么这个证候,什么样子呢?“不大便,烦躁发热”,切脉呢,比较实“微实”不是又微又实,微微实,实得也不太厉害。“再倍发热”,但是发热有一个定时。它这是倒装句,应该是“日晡时烦躁者,再倍发热”,它在日晡所的时候,发热加倍。它这是倒装句,古人的文章这样的很多,不要被原来句子的句读给弄糊涂了。它本来就烦躁发热,到这个日哺所的时候,就是日将落这是阳明病的一个证候,这个时候烦躁发热都加倍。“不食”,阳明篇讲得很多了,要是开始得阳明病,这里头有寒,又是有水了,中寒者不能食嘛,它里头有东西了也不能吃;真正是热,热实于里,它就大便干了,也不能食。这个不食,就是指后头这种,它里头有东西而吃不下去,一吃呢,就要说胡话,“食则谵语”,说胡话就是胃不和嘛。
“至夜即愈”,这个辨证辨得多好啊,至夜即愈说明什么问题啊?这不是恶露自己在那个地方搞成郁热了。这个血证啊,你看热入血室,昼而安静,到夜间如见鬼状,瘀血证,郁热都在夜间,白天好;阳明病不是这样的,阳明病日晡所厉害,到夜间反倒好了。所以它说至夜即愈,它指的是再倍发热这个情况,它一到夜间就好了。这说明什么,这就是辨证,主要的热是在里,并不在血实,这底下有解释,干脆用大承气汤,不必搁其他的祛瘀药。什么道理呢?就是“热在里”,就由于里太热了,使得这恶露结而不行,“结在膀胱也它不是在膀胱这个部位先蕴热而结,它是由于里热,换言之由于阳明病,一吃大承气汤,阳明里热一解,这个血自行。这多好啊!“至夜即愈”不是废话,这就是得辨证。要记得:瘀热这种情况都是夜间多,而在白天(病情则)挺好,所以这书要前后看,你看热入血室它是白天好,夜间厉害。
那这为什么用大承气汤呢?它是这么个道理:如果这恶露不尽在于恶露自为病,那我们用可下的(诸如)桃仁承气汤什么都行;不可下的用桂枝丸什么的也行啊,都可以祛恶露嘛。但是,它不是恶露自为病,纯粹受阳明里热的影响,导致恶露结而不行,这种情况用大承气汤就可以了。这个地方都挺好,辨证给人很多启示。
那么到这儿把腹痛讲完了。还有一种恶露不尽的腹痛,这在产后是最常见的。对于恶露不尽,他特意举了一个大承气汤证,由于里热造成的,其他的一般情况不是没有,而是没说,所以这一段我认为非常精彩。不是一般的(情况)没有了,而是没多说啊!(说过的)像有个下瘀血汤等,其他学过的祛瘀药都有可用的机会了,有那个相应的证就行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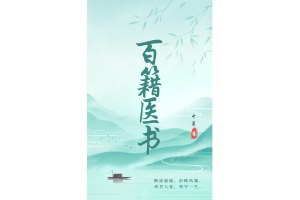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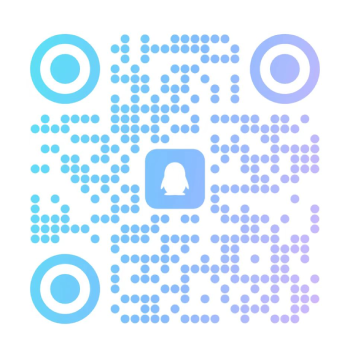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