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今名医方论
罗美
刻方论小序
自昔彼美云遐,良遘难再,士生其间,动成慨往,无叩角短骭之谣,有带月归锄之兴。是以陆沉之志,思似长沮;麋鹿之情,实甘丰草。微吟午夜,耿怀人至曙星;齁梦北窗,享羲皇于肱半。虽或果哉,终斯己矣。无如大壑沦漂,蓬茨渊浸,三时或馁,九稔恒饥,则又去而逃死,悬壶给食。于是始为医学,搜时传之秘简,阅指掌之授书,见其类证,为编括方。以口尘轩岐于庋坫,霾长沙以云雾。转益膏肓,徒增横夭。仲景不云乎,人禀五常,以有五脏,经络府俞,阴阳会通,玄冥幽微,变化难极,自非才高识妙,岂能探其理致?今之学医,不思识字,讨论经旨,以演其所知,而乃面墙窥管,费人试方,老者不愧,少而无知,痛心哉!不揣不敏,每循斯事,思欲究并阖之玄枢,抉参同于符易。日与同志数公,旁搜远绍,始自汉代,下迄元明,无下百家,要归一辙,作用底蕴,颇能灿然,因集为《古今名医经论证治汇粹》八卷。方论在其末编,今令先出,请正同学。以诸医方所集,要约简明,皆日用常行,昭昭耳目,用之恒常而易忽,体以证治而或非,虽人人拈,未事事当,用将以为耳前之嚆矢,眸畔之电光,野人搜集,聊涧芹之一献云尔。其于漏卮无当,固稿项黄馘之所固然,而无足道也。因序。
时康熙乙卯巧月既望
新安罗美书于虞山麓之古怀堂
凡例
——古之方书,得人乃传,非人勿言,诚重之也。故扁鹊仓公辈,皆称禁方,不轻授人。后汉张仲景夫子,伤横夭之莫救,博采众方,平脉辨证,著《伤寒杂病论》,公之天下,欲人见病思源,是世医方之祖也。其方发表攻里,固本御邪,内外证治,无乎不备。后人惑伤寒为一家书,束之高阁。即专治伤寒者,又为《活人》《全生》诸书所掩,未尝好学深思,心知其故。则见为古方难用,竞营肤浅,以矜捷得,所以瓦釜雷鸣也。兹编本欲以仲景方为首简,恐人犹重视而畏远之,姑以日用诸方表表耳目者为先导。诸方义明,而后入仲景之门,亦行远登高之自尔。
——汉建安以前,苦于无方;宋元丰以后,《局方》猥赜,蔓延今时,何有根柢,漫无指归。惟薛立斋先生所用诸方,简严纯正,可为后法,是编多所采录。而《金匮》《千金》《外台》诸书,及洁古、东垣、太无、丹溪方之佳者,咸择而录焉。仲景有云:学者能寻余所集,思过半矣。
——有方即有柄,自仲景始也;有方更有论,自成无己始也。明代赵以德有《金匮衍义》,于方颇有论,吴氏鹤皋著《医方考》,近时医林复有张景岳、赵养葵、喻嘉言、李士材、程郊倩、张路玉、程扶生诸公,各有发明,余喜得而集之矣。然其间或择焉而未精,语焉而未详,亦间有不惬于心者。因与素交诸同人,往来探索古作者之意,时时析疑欣赏,得见一斑,即各与分方补论,因而附列增入,少开后学。本非啖名,实未辞续貂之愧云。
——病名多端,不可以数计,故仲景分六经而司治之,使百病咸归六经,是扼要法也。后人不知六经为杂病辨证设,竟认为伤寒设,由是仲景辨证之权衡废。夫不知证,便不知方矣。巢元方作《病源》,陈无择作《三因》,为近来医书之祖;华佗之《肘后》,孙思邈之《千金》,是后来《局方》之祖。然论虽多,方虽广,而不得治之要,实千载迷途矣。后此继起者,莫不贵叙证之繁,治法之备,集方之盛,求胜前人。不知病名愈多,后学愈昏;方治愈繁,用者愈无把柄。一遇盘根错节,遍试诸方,眇无所措。岂如得仲景法,不于诸病搜索,但于六经讲求,一剂而唾手可愈耶。友人韵伯,于仲景书探讨有年,所著《伤寒论翼》,多所发明。故是编于伤寒方中,录其论最多,亦欲学者因之略见仲景一斑耳。
——吴氏作《医方考》,其意未尝不欲以立方本源,开后学之蒙也。究乃拘证论方,譬多疏注以迁就之,仍与诸家类书无别。夫所谓考者,考其制方之人,命名之义,立方之因,与方之用,因详其药之品味,分两制度,何病是主治,何病可兼治,何病当增减,何病不可用,使人得见之明,守之固也。乃尔分门分方,第知有证之可寻,徒列方以备员,亦何知有方之神奇变化,考其所用之精妙乎?是编非但论其方之因,方之用,详其药性,君臣法制,命名之义而已,必论其内外新久之殊,寒热虚实之机,更引诸方而比类之,又推本方而互通之。论一病而不为一病所拘,明一方而得众病之用,游于方之中,超乎方之外,全以活法示人,比之《方考》,稍有一得耳。
——僭评方论,非取文章。故所批阅,必于眼目肯綮,指出所以然,以质证同志。人有共目,则人有同心,非敢僭为臆说也。
——兹选,不侫本以数年心目,遍搜古今名医经论,删纂其要,定为《古今名医汇粹》八卷,实为经论无方之书。兹选《方论》附在末部,因剞劂费繁,兹编先出,用质四方同志。以为可教,祈珠玉见投,以慰饥渴,即当补入正集,用庆大观。
卷一
补中益气汤
治阴虚内热,头痛,口渴,表热自汗,不任风寒,脉洪大,心烦不安,四肢困倦,懒于言语,无气以动,动则气高而喘。
黄芪 人参 云术 炙甘草 陈皮 当归 升麻 柴胡
上八味,加生姜三片,大枣二枚,水煎,温服。
柯韵伯曰:仲景有建中、理中二法。风木内干中气,用甘草、饴、枣培土以御风,姜、桂、芍药驱风而泻木,故名曰建中。寒水内凌于中气,用参、术、甘草补土以制水,佐干姜而生土以御寒,故名曰理中。至若劳倦,形气衰少,阴虚而生内热者,表症颇同外感,惟东垣知其为劳倦伤脾,谷气不盛,阳气下陷阴中而发热,制补中益气之法。谓风寒外伤其形为有余,脾胃内伤其气为不足,遵《内经》劳者温之损者益之之义,大忌苦寒之药,选用甘温之品,升其阳以行春生之令。凡脾胃一虚,肺气先绝,故用黄芪护皮毛而开腠理,不令自汗;元气不足,懒言,气喘,人参以补之;炙甘草之甘以泻心火而除烦,补脾胃而生气。此三味除烦热之圣药也。佐白术以健脾;当归以和血;气乱于胸,清浊相干,用陈皮以理之,且以散诸甘药之滞;胃中清气下沉,用升麻、柴胡,气之轻而味之薄者,引胃气以上腾,复其本位,便能升浮以行生长之令矣。补中之剂,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;益气之剂,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。此用药有相须之妙也。是方也,用以补脾,使地道卑而上行;亦可以补心肺,损其肺者益其气,损其心者调其营卫也;亦可以补肝木,郁则达之也。惟不宜于肾,阴虚于下者不宜升,阳虚于下者更不宜升也。凡东垣治脾胃方,俱是益气。去当归、白术,加苍术、木香,便是调中;加麦冬、五味辈,便是清暑。此正是医不执方,亦是医必有方。
赵养葵曰:后天脾土,非得先天之气不行。此气因劳而下陷于肾肝,清气不升,浊气不降,故用升、柴以佐参、芪,是方所以补益后天中之先天也。(益后天中之先天,后人未发。)凡脾胃喜甘而恶苦,喜补而恶攻,喜温而恶寒,喜通而恶滞,喜升而恶降,喜燥而恶湿。此方得之。
陆丽京曰:此为清阳下陷者言之,非为下虚而清阳不升者言之也。倘人之两尺虚微者,或是癸水销竭,或是命门火衰,若再一升提,则如大木将摇而拔其本也。(此韵伯所谓独不宜于肾也。)
周慎斋曰:下体痿弱,虚弱者不可用补中,必当以八味丸治之。凡内伤作泻,藏附子于白术中,令其守中以止泄也;表热,藏附子于黄芪中,欲其走表以助阳也。
卷一
黄芪建中汤
治虚劳里急,悸,衄,腹中痛,梦失精,四肢酸疼,手足烦热,咽干口燥,诸不足。
黄芪 胶饴 白芍 甘草 桂枝 生姜 大枣
上七味,水煎服。
喻氏曰:虚劳而至于亡血失精,津液枯槁,难为力矣。《内经》于针药所莫制者,调以甘药。《金匮》遵之而用黄芪建中汤,急建其中气,俾饮食增而津液旺,以至充血生精,而复其真阴之不足。但用稼穑作甘之本味,而酸辛咸苦在所不用,盖舍此别无良法也。然用法贵立于无过之地,宁但呕家不可用建中之甘,即服甘药,微觉气阻气滞,更当虑甘药太过,令人中满,早用陈皮、砂仁以行之可也。不然,甘药又不可恃,更将何所恃哉?后人多用乐令建中汤、十四味建中汤,虽无过甘之弊,然乐令方中前胡、细辛为君,意在退热,而阴虚之热则不可退;十四味方中用附、桂、苁蓉,意在复阳,而阴虚之阳未必可复,又在用方之善为裁酌矣。
又曰:伤寒有小建中一法,治二三日心悸而烦,以其人中气馁弱,不能送邪外出,故用饴糖之甘,小小建立中气以祛邪也。《金匮》有黄芪建中一法,加黄芪治虚劳里急,自汗,表虚,肺虚,诸不足症,而建其中之卫气也。《金匮》复有大建中一法,以其人阴气上逆,胸中大寒,呕不能食,而腹痛至极,用蜀椒、干姜、人参、饴糖,大建其中之阳,以驱逐浊阴也。后人复广其义,曰:乐令建中汤,治虚劳发热,以之并建其中之荣血。曰:十四味建中汤,治脏气里虚,以之两建其脾中肾中之阳阴。仲景为祖,后人为孙,使虚羸之体,服建中之后,可汗可下,诚足恃也。至理中,则燮理之义;治中,则分治之义;补中、温中,莫非惠先京国之义。缘伤寒外邪逼域中,法难尽用,仲景但于方首,以小之一字,示其微义,至《金匮》始尽建中之义。后人引伸触类,曲畅建中之旨。学者心手之间,所当会其大义也。
卷一
人参养荣汤
治脾肺俱虚,发热恶寒,肢体瘦倦,食少作泻等症。若气血虚而变见诸症,勿论其病其脉,但用此汤,诸症悉退。
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 黄芪 陈皮 当归 熟地 白芍 五味子 桂心 远志
上十二味,加姜三片,枣二枚,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古人治气虚以四君,治血虚以四物,气血俱虚者以八珍,更加黄芪、肉桂,名十全大补,宜乎万举万当也。而用之有不获效者,盖补气而不用行气之品,则气虚之甚者,无气以受其补;补血而仍用行血之物于其间,则血虚之甚者,更无血以流行。(议方确妙。)故加陈皮以行气,而补气者,悉得效其用;去川芎行血之味,而补血者,因以奏其功。此善治者,只一加一减,便能转旋造化之机也。然气可召而至,血易亏难成,苟不有以求其血脉之主而养之,则营气终归不足,故倍人参为君,而佐以远志之苦,先入心以安神定志,使甘温之品,始得化而为血,以奉生身。又心苦缓,必得五味子之酸以收敛神明,使营行脉中而流于四脏,名之曰养荣,不必仍十全之名,而收效有如此者。
卷一
归脾汤
治思虑伤脾,或健忘,怔忡,惊悸,盗汗,寤而不寐;或心脾作痛,嗜卧,少食,月经不调。
人参 黄芪 甘草 白术 茯苓 木香 龙眼肉 酸枣仁 当归 远志
姜三片,水煎服。
罗东逸曰:方中龙眼、枣仁、当归,所以补心也;参、芪、术、苓、草,所以补脾也。立斋加入远志,又以肾药之通乎心者补之,是两经兼肾合治矣。而特名归脾,何也?夫心藏神,其用为思;脾藏智,其出为意;是神智思意,火土合德者也。心以经营之久而伤,脾以意虑之郁而伤,则母病必传诸子,子又能令母虚,所必然也。其症则怔忡、怵惕、烦躁之征见于心;饮食倦怠,不能运思,手足无力,耳目昏眊之症见于脾。故脾阳苟不运,心肾必不交。彼黄婆者若不为之媒合,则已不能摄肾归心,而心阴何所赖以养?此取坎填离者,所以必归之脾也。其药一滋心阴,一养脾阳,取乎健者,以壮子益母;然恐脾郁之久,伤之特甚,故有取木香之辛且散者,以闿气醒脾,使能急通脾气,以上行心阴。脾之所归,正在斯耳!
张路玉曰:补中益气与归脾,同出保元,并加归、术,而有升举胃气,滋补脾阴之不同。此方滋养心脾,鼓动少火,妙以木香调畅诸气。世以木香性燥不用,服之多致痞闷,或泄泻、减食者,以其纯阴无阳,不能输化药力故耳!
卷一
保元汤
治气虚血弱之总方也。小儿惊痘家虚者最宜。
黄芪三钱 人参二钱 甘草一钱 肉桂春夏二三分,秋冬六七分
上四味,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保元者,保守其元气之谓也。气一而已,主肾,为先天真元之气;主胃,为后天水谷之气者。此指发生而言也。又水谷之精气,行于经隧为营气;水谷之悍气,行于脉外为卫气;大气之积于胸中而司呼吸者为宗气。是分后天运用之元气而为三也。又外应皮毛,协营卫,而主一身之表者,为太阳膀胱之气;内通五脏,司治节,而主一身之里者,为太阴肺经之气;通行内外,应腠理,而主一身之半表半里者,为少阳三焦之气。是分先天运行之元气而为三也。(条分诸气,足开后学之蒙。)此方用黄芪护表,人参固里,甘草和中,三气治而元气足矣。昔李东垣以此三味,能泻火、补金、培土,为除烦热之圣药;镇小儿惊,效如桴鼓。魏桂岩得之,以治痘家阳虚顶陷,血虚浆清,皮薄发痒,难灌难敛者,始终用之。以为血脱须补气,阳生则阴长,有起死回生之功,故名之为保元也。又少佐肉桂,分四时之气而增损之,谓桂能治血,以推动其毒,扶阳益气,以充达周身。血在内,引之出表,则气从内托;血外散,引之归根,则气从外护。参、芪非桂引道,不能独树其功;桂不得甘草和平气血,亦不能绪其条理。要非寡闻浅见者,能窥其万一也。四君中不用白术,避其燥;不用茯苓,恐其渗也。用桂而不用四物者,芎之辛散,归之湿润,芍之酸寒,地黄之泥滞故耳。如宜燥则加苓、术,宜润加归,宜收加芍,当散加芎。又表实去芪,里实去参,中满忌甘,内热除桂,斯又当理会矣。(推明加减,其法灿然。)
又云:人知火能克金,而不知气能胜火;人知金能生水,而不知气即是水。此义惟东垣知之,故曰参、芪、甘草,除烦热之圣药。要知气旺则火邪自退。丹溪云气有余便是火,不知气上腾便是水。(妙理独发。)
卷一
四君子汤
治面色痿白,言语轻微,四肢无力,脉来虚弱者。若内热,或饮食难化作酸,乃属虚火,须加炮姜。
人参 白术 茯苓 甘草各二钱
水煎,加姜、枣。
加陈皮,为五味异功散。加陈皮、半夏,为六君子汤。
张路玉曰:气虚者补之以甘,参、术、苓、草,甘温益胃,有健运之功,具冲和之德,故为君子。若合之二陈,则补中微有消导之意。盖人之一身,以胃气为本。胃气旺,则五脏受荫;胃气伤,则百病丛生。故凡病久不愈,诸药不效者,惟有益胃、补肾两途。故用四君子随症加减,无论寒热补泻,先培中土,使药气四达,则周身之机运流通,水谷之精微敷布,何患其药之不效哉!是知四君、六君为司命之本也。更加砂仁、木香,名香砂六君子。
卷一
香砂六君子汤
治气虚肿满,痰饮结聚,脾胃不和,变生诸症者。
人参一钱 白术二钱 茯苓二钱 甘草七分 陈皮八分 半夏一钱 砂仁八分 木香七分
上生姜二钱,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经曰:"壮者气行则愈,怯者著而为病。"盖人在气交之中,因气而生,而生气总以胃气为本。食入于阴,长气于阳,昼夜循环,周于内外。一息不运,便有积聚,或胀满不食,或生痰留饮,因而肌肉消瘦,喘咳呕哕,诸症蜂起,而神机化绝矣。四君子气分之总方也,人参致冲和之气,白术培中宫,茯苓清治节,甘草调五脏,诸气既治,病安从来?然拨乱反正,又不能无为而治,必举夫行气之品以辅之,则补品不至泥而不行。故加陈皮以利肺金之逆气,半夏以疏脾土之湿气,而痰饮可除也;加木香以行三焦之滞气,缩砂以通脾肾之元气,膹郁可开也。四君得四辅,而补力倍宣;四辅有四君,而元气大振。相须而益彰者乎!
卷一
四物汤
治一切血虚、血热、血燥诸症。
当归 熟地各三钱 川芎一钱五分 白芍二钱,酒炒
上四味,水煎服。
张路玉曰: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,非调补真阴之的方。方书咸谓四物补阴,遂以治阴虚发热,火炎失血等证,蒙害至今。又专事女科者,咸以此汤随症漫加风、食、痰、气等药,纷然杂出。其最可恨者,莫如坎离丸之迅扫虚阳,四物二连之斩削真气,而庸工利其有劫病之能,咸乐用之,何异于操刃行劫耶!先辈治上下失血过多,一切血药置而不用,独推独参汤、童便以固其脱者,以有形之血不能速生,无形之气所当急固也。昔人有言,见血无治血,必先调其气。又云,四物汤不得补气药,不能成阳生阴长之功。诚哉言也!然余尝谓此汤,伤寒火邪解后,余热留于血分,至夜微热不除,或合柴胡,或加桂枝,靡不应手辄效,不可没其功也。
卷一
圣愈汤
治一切失血,或血虚烦渴燥热,睡卧不宁,五心烦热,作渴等症。
四物汤加人参、黄芪。一方去芍药。
上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经曰:"阴在内,阳之守也;阳在外,阴之使也。"故阳中无阴,谓之孤阳;阴中无阳,谓之死阴。丹溪曰:四物皆阴,行天地闭塞之令,非长养万物者也。故四物加知、柏,久服便能绝孕,谓其嫌于无阳耳!此方取参、芪配四物,以治阴虚、血脱等症。盖阴阳互为其根,阴虚则阳无所附,所以烦热燥渴,而阳亦亡;气血相为表里,血脱则气无所归,所以睡卧不宁,而气亦脱。然阴虚无骤补之法,计在存阳;血脱有生血之机,必先补气。此阳生阴长,血随气行之理也。故曰阴虚则无气,无气则死矣。此方得仲景白虎加人参之义而扩充者乎!前辈治阴虚,用八珍、十全,卒不获效者,因甘草之甘,不达下焦;白术之燥,不利脾肾;茯苓渗泄,碍乎生升;肉桂辛热,动其虚火。此六味,皆醇厚和平而滋润,服之则气血疏通,内外调和,合于圣度矣。
卷一
当归补血汤
治男妇肌热,面赤,烦渴引饮,脉来洪大而虚,重按全无。
当归二钱 黄芪一两
水煎服。
吴鹤皋曰:血实则身凉,血虚则身热。或以饥困劳役,虚其阴血,则阳独治,故诸症生焉。此证纯象白虎,但脉大而虚,非大而长为辨耳!《内经》所谓脉虚血虚是也。当归味厚,为阴中之阴,故能养血。黄芪则味甘,补气者也。今黄芪多数倍,而云补血者,以有形之血,不能自生,生于无形之气故也。《内经》云阳生阴长,是之谓耳!
卷一
酸枣仁汤
治虚劳虚烦不得眠。
酸枣仁二升 甘草一两 知母二两 茯苓二两 川芎二两
上五味,以水八升,煮枣仁得六升,纳药煮取三升,分温三服。
罗东逸曰:经曰:"肝藏魂","人卧则血归于肝"。又曰:"肝者,罢极之本。"又曰:"阳气者,烦劳则张,精绝。"故罢极必伤肝,烦劳则精绝,肝伤、精绝则虚劳虚烦不得卧明矣。枣仁酸平,应少阳木化,而治肝极者,宜收宜补,用枣仁至二升,以生心血、养肝血,所谓以酸收之,以酸补之是也。顾肝郁欲散,散以川芎之辛散,使辅枣仁通肝调营,所谓以辛补之。肝急欲缓,缓以甘草之甘缓,防川芎之疏肝泄气,所谓以土葆之。然终恐劳极,则火发于肾,上行至肺,则卫不合而仍不得眠,故以知母崇水,茯苓通阴,将水壮金清而魂自宁,斯神凝魂藏而魄且静矣。此治虚劳肝极之神方也。
卷一
养心汤
治心神不足,梦寐不宁,惊悸,健忘等症。
白芍 当归 人参 远志 麦门冬 黄芩 山药 芡实 莲须 酸枣仁 茯神 石莲子
上十二味,水煎服。
吴于宣曰:《难经》云:心不足者,调其荣卫。荣卫者,血脉之所出,而心主之。故养心者,莫善于调荣卫也。然荣卫并出中州,荣淫精于肝,而浊气归心;卫气通于肺,而为心相;肾受心营肺卫之归,而又升精于离,以成水火既济。是三脏者,皆心之助,而调荣卫者,所必出于是也。故调荣卫,调其四脏,而心养矣。是方人参、茯神以神养心,枣仁、归、芍以母养肝,山药、门冬、黄芩以清养肺,莲须、芡实、石莲、远志以涩养精而升之,于是神明之君主,泰然于天钧之上矣。此养心之旨也。
卷一
独参汤
治元气虚而不支,脉微欲绝,及妇人血崩,产后血晕。
人参分两随人随症
须上拣者浓煎顿服,待元气渐回,随症加减。
柯韵伯曰:一人而系一世之安危者,必重其权而专任之;则一物而系一人之死生者,当重其分两而独用之。《春秋运斗枢》云:摇光星散而为人参。所以下有人参,上有紫气,物华天宝,洵神物也。故先哲于气虚血脱之证,独用人参三两,浓煎顿服之,能挽回性命于瞬息之间,非他物所可代。世之用者,恐或补住邪气,些少以姑试之,或加消耗之味以监制之,其权不重,力不专,人何赖以得生?(无论庸工莫知其理,即负盛名者,尚习焉不察,可叹!)如古方霹雳散、独圣散、大补丸、举卿古拜等方,皆用一物之长,而取效最捷,于独参汤何疑耶?然又当随机应变,视病机为转旋。故独参汤中,或加童便,或加姜汁,或加附子,或加黄连,相得相须,而相与有成,亦不碍其为独。如薛新甫治中风,加人参两许于三生饮中,以驾驭其抑,此真善用独参汤者。
卷一
炙甘草汤
治伤寒脉结代,心动悸者。《外台》又治肺痿,咳吐多,心中温温液液者。
甘草四两,炙 生地黄一斤 麦冬半斤 人参一两 桂枝三两 生姜二两 大枣十二枚 阿胶二两 麻仁半斤
上九味,以酒七升,水八升,煮取三升,去滓,入胶溶尽,温服一升,日三服。一名复脉汤。
喻嘉言曰:按此汤仲景伤寒门治邪少虚多,脉结代,心动悸之圣方也。一名复脉汤。《千金翼》用之以治虚劳。《外台》用之以治肺痿。然本方所治,亦何止于二病?仲景诸方,为生心之化裁,亦若是而已矣。《外台》所取,在于益肺气之虚,润肺金之燥。至于桂枝辛热,似有不宜。而不知桂枝能通营卫,致津液,营卫通,津液致,则肺气转输,浊沫以渐而下,尤为要药,所以云治心中温温液液者。
柯韵伯曰:仲景于脉弱者,用芍药以滋阴,桂枝以通血,甚则加人参以生脉,未有用地黄、麦冬者,岂以伤寒之法,义重扶阳乎?抑阴无骤补之法与?此以心虚脉代结,用生地为君,麦冬为臣,峻补真阴,开后学滋阴之路。地黄、麦冬味虽甘而气大寒,非发陈蕃秀之品,必得人参、桂枝以通脉,生姜、大枣以和营,阿胶补血,酸枣安神,甘草之缓不使速下,清酒之猛捷于上行,内外调和,悸可宁而脉可复矣。酒七升,水八升,只取三升者,久煎之则气不峻,此虚家用酒之法,且知地黄、麦冬得酒良。
卷一
逍遥散
治肝家血虚火旺,头痛,目眩,颊赤,口苦,倦怠,烦渴,抑郁不乐,两胁作痛,寒热,小腹重坠,妇人经水不调,脉弦大而虚。
当归 芍药酒炒 白术炒 茯苓 甘草炙 柴胡各一钱
加味逍遥散,即此方加丹皮、山栀炒,各五分。
赵羽皇曰:五脏苦欲补泻云:肝苦急,急食甘以缓之。盖肝性急,善怒,其气上行则顺,下行则郁,郁则火动,而诸病生矣。故发于上则头眩、耳鸣,而或为目赤;发于中则胸满、胁痛,而或作吞酸;发于下则少腹疼疝,而或溲溺不利;发于外则寒热往来,似疟非疟。凡此诸症,何莫非肝郁之象乎?(治肝之法尽矣。)而肝木之所以郁者,其说有二:一为土虚不能升木也,一为血少不能养肝也。盖肝为木气,全赖土以滋培,水以灌溉。若中气虚,则九地不升,而木因之郁;阴血少,则木无水润,而肝遂以枯。(养葵曰:人知木克土,不知土升木,知言哉!)方用白术、茯苓者,助土德以升木也;当归、芍药者,益荣血以养肝也;丹皮解热于中,草、栀清火于下。独柴胡一味,一以厥阴报使,一以升发诸阳。经云:木郁则达之。柴胡其要矣!
卷一
二陈汤
治肥盛之人,湿痰为患,喘嗽,胀满。
半夏三钱 茯苓三钱 陈皮去白,三钱 甘草一钱
上四味,加姜三片,水煎服。
李士材曰:肥人多湿,湿挟热而生痰,火载气而逆上。半夏之辛,利二便而去湿;陈皮之辛,通三焦而理气;茯苓佐半夏,共成燥湿之功;甘草佐陈皮,同致调和之力。成无己曰:半夏行水气而润肾燥,经曰辛以润之是也。行水则土自燥,非半夏之性燥也。(半夏议明晰。)或曰有痰而渴,宜去半夏,代以贝母。
吴鹤皋曰:渴而喜饮者易之,不能饮水,虽渴宜半夏也。此湿为本,热为标,所谓湿极而兼胜己之化,非真象也。又东南之人,湿热生痰,故丹溪恒主之。加枳实、砂仁,即名枳砂二陈汤,其性较急也。先哲曰:二陈为治痰之妙剂,其于上下左右,无所不宜。然止能治痰之标,不能治痰之本。痰本在脾在肾,治者详之。
卷一
生脉散
治热伤元气,气短,倦怠,口干,出汗。
人参 麦门冬 五味子
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肺为娇脏而朝百脉,主一身元气者也。形寒饮冷则伤肺,故伤寒有脉结代与脉微欲绝之危;暑热刑金则伤肺,故伤热有脉来虚散之足虑。然伤寒是从前来者,为实邪,故虽脉不至,而可复可通;伤热是从所不胜来者,为贼邪,非先从滋化其源,挽回于未绝之前,则一绝而不可复。此孙真人为之急培元气,而以生脉名方也。麦冬甘寒,清权衡治节之司;人参甘温,补后天营卫之本;五味酸温,收先天天癸之原。三气通而三才立,水升火降,而合既济之理矣。
仲景治伤寒,有通脉、复脉二法。少阴病里寒外热,下利清谷,脉微欲绝者,制通脉四逆汤,温补以扶阳;厥阴病外寒内热,心动悸,脉结代者,制复脉汤,凉补以滋阴。同是伤寒,同是脉病,而寒热异治者,一挽坎阳之外亡,一清相火之内炽也。生脉散本复脉立法,外无寒,故不用姜、桂之辛散;热伤无形之气,未伤有形之血,故不用地黄、阿胶、麻仁、大枣,且不令其泥膈而滞脉道也。心主脉而苦缓,急食酸以收之,故去甘草而加五味矣。脉资始于肾,资生于胃,而会于肺。仲景二方重任甘草者,全赖中焦谷气,以通之复之,非有待于生也。此欲得下焦天癸之元气以生之,故不藉甘草之缓,必取资于五味之酸矣。
卷一
理中汤
治中气不运,腹中不实,口失滋味,病久不食,脏腑不调,与伤寒直中太阴,自利不渴,寒多而呕等证。
人参 白术 干姜炮 甘草炙,各一钱五分
水煎服。加附子,即名附子理中汤。
程郊倩曰:阳之动,始于温,温气得而谷精运,谷气升而中气赡,故名曰理中。实以燮理之功,予中焦之阳也。若胃阳虚,即中气失宰,膻中无发宣之用,六腑无洒陈之功,犹如釜薪失焰,故下至清谷,上失滋味,五脏凌夺,诸症所由来也。参、术、炙草,所以固中州;干姜辛以守中,必假之以焰釜薪而腾阳气。是以谷入于阴,长气于阳,上输华盖,下摄州都,五脏六腑皆以受气矣。此理中之旨也。若水寒互胜,即当脾肾双温,附子之加而命门益,土母温矣。
卷一
《三因》附、术附、参附三汤
治阳虚自汗,寒湿沉痼,阳虚阴盛。
黄芪一两 附子五钱 名芪附汤。
白术一两 附子五钱 名术附汤。
人参一两 附子五钱 名参附汤。
水煎,分三服。
喻嘉言曰:卫外之阳不固而自汗,则用芪附;脾中之阳遏郁而自汗,则用术附;肾中之阳浮游而自汗,则用参附。凡属阳虚自汗,不能舍三方为治。然三方之用大矣,芪附可以治虚风,术附可以治寒湿,参附可以壮元神,三者亦交相为用。若用其所当用,功效若神,诚足贵也。以黄芪、人参为君,其长驾远驭,附子固不足以自恣,术虽不足以制附,然遇阳虚阴盛,寒湿沉痼,即生附在所必用,何取制伏为耶?《金匮》白术附子汤中,加甘草一味,以治痹症,岂非节制之师乎?急症用其全力,即不可制;缓症用其半力,即不可不制。至如急中之缓,缓中之急,不制而制,制而不制,妙不能言。
卷一
清暑益气汤
长夏湿热蒸炎,四肢困倦,精神减少,身热,气高,烦心,便黄,渴而自汗,脉虚者,此方人参 黄 甘草 白术 苍术(一钱五分) 神曲 青皮 升麻 干葛 麦冬 五味当归 黄柏 泽泻吴鹤皋曰:暑令行于夏,至长夏则兼湿令矣。此方兼而治之。炎暑则表气易泄,兼湿则中气麦津液亡则口渴,故以当归、干葛生其胃液;清气不升,升麻可升;浊气不降,二皮可理;苍术之用,为兼长夏湿也。
程郊倩曰:人知清暑,我兼益气,以暑伤气也。益气不独金能敌火,凡气之上腾,而为津为
卷一 清暑益气汤
长夏湿热蒸炎,四肢困倦,精神减少,身热,气高,烦心,便黄,渴而自汗,脉虚者,此方主之。
人参 黄芪 甘草 白术 苍术一钱五分 神曲 青皮 升麻 干葛 麦冬 五味 当归 黄柏 泽泻 广皮
水煎,温服。
吴鹤皋曰:暑令行于夏,至长夏则兼湿令矣。此方兼而治之。炎暑则表气易泄,兼湿则中气不固,黄芪所以实表,白术、神曲、甘草所以调中;酷暑横流,肺金受病,人参、五味、麦冬所以补肺、敛肺、清肺,经所谓扶其所不胜也;火盛则水衰,故以黄柏、泽泻滋其化源;津液亡则口渴,故以当归、干葛生其胃液;清气不升,升麻可升;浊气不降,二皮可理;苍术之用,为兼长夏湿也。
程郊倩曰:人知清暑,我兼益气,以暑伤气也。益气不独金能敌火,凡气之上腾,而为津为液者,向下即肾中之水,水气足,火淫自却也。
〖附:暑门诸方论〗
喻嘉言曰:元丰朝立和剂局,萃集医家经验之方,于中暑一门独详。以夏月暑证,五方历试,见闻广耳。其取用小半夏茯苓汤,不治其暑,专治其湿。又以半夏、茯苓,少加甘草,名消暑丸,见消暑在消其湿矣。其香薷饮,用香薷、扁豆、厚朴为主方,热盛则去扁豆,加黄连为君,治其心火;湿甚则去黄连,加茯苓、甘草,治其脾湿。其缩脾饮,则以脾为湿所浸淫而重滞,于扁豆、葛根、甘草中,佐以乌梅、砂仁、草果,以快脾而去脾所恶之湿。甚则用大顺散、来复丹,以治暑证之多泻利者,又即缩脾之意而推之也。其枇杷叶散,则以胃为湿所窃据而浊秽,故用香薷、枇杷叶、丁香、白茅香之辛香,以安胃而去胃所恶之臭。甚则用冷香引子,以治暑证之多呕吐者,又即枇杷叶散而推之也。医者于湿热虚寒,浅深缓急间,酌而用之,其利溥矣。而后来诸贤,以益虚继之。河间之桂苓甘露饮,五苓三石,意在生津液以益胃之虚。子和之桂苓甘露饮,用人参、甘草、葛根、藿香、木香,益虚之中又兼去浊;或用十味香薷饮,于《局方》五味中,增人参、黄芪、白术、陈皮、木瓜,益虚以去湿热。乃至东垣之清暑益气汤、人参黄芪汤,又补中实卫以去其湿热,肥白内虚之人,勿论中暑与否,所宜频服者也。中暑必显躁烦热闷,东垣仿仲景竹叶石膏汤之制,方名清燥汤,仍以去湿为首务。夫燥与湿,相反者也,而清燥亦务除湿,非东垣具过人之识,不及此矣。又如益元散之去湿,而加辰砂则并去其热;五苓散之去湿,而加人参则益虚,加辰砂减桂则去热;白虎汤加人参则益虚,加苍术则胜湿。合之《局方》,则大备矣。然尚有未备者,暑风一症,猝倒类乎中风,而未可从风门索治。《百一选方》大黄龙丸,初不为暑风立法,而愚见从而赞之曰:有中暍昏死,灌之立苏。此可得治暑风一斑矣。倘其人阴血素亏,暑毒深入血分者,《良方》复有地榆散。治中暑昏迷,不省人事而欲死者,但用平常凉血之药,清解深入血分之暑风。此以心火暴甚,煎熬真阴,舍清心凉血之外,无可泼灭者,美其名曰泼火散,知言哉!
卷一
竹叶黄芪汤
治消渴,气血虚,胃火盛而作渴。
淡竹叶 生地黄各二钱 黄芪 麦冬 当归 川芎 黄芩 甘草 芍药 人参 半夏 石膏各一钱
上水煎服。
柯韵伯曰:气血皆虚,胃火独盛,善治者补泻兼施,寒之而不致亡阳,温之而不至于助火,扶正而邪却矣。四君子气药也,加黄芪而去苓、术,恐火就燥也。四物汤血药也,地黄止用生者,正取其寒也。人参、黄芪、甘草治烦热之圣药,是补中有泻矣。且地黄之甘寒,泻心肾之火,竹叶助芍药清肝胆之火,石膏佐芍药清脾胃之火,麦冬同黄芩清肺肠之火,则胃火不得独盛,而气血之得补可知。惟半夏一味,温中辛散,用之大寒剂中,欲其通阴阳之路也。岐伯治阴虚而目不瞑者,饮以半夏汤,覆杯则卧。今人以为燥而渴者禁用,是不明阴阳之理耳!
卷一
清燥救肺汤
(喻氏制。论一条)
主治诸气愤郁,诸痿喘呕。
桑叶经霜者,三钱 石膏二钱五分,煅 甘草一钱 人参七分 胡麻仁一钱,炒研 真阿胶八分 麦冬一钱二分 杏仁去皮尖,炒黄,七分 枇杷叶去毛蜜炙,用一片
上九味,以水一碗,煎六分,频频二三次滚热服。痰多加贝母、瓜蒌。血枯加生地。热甚加犀角、羚羊角,或加牛黄。
喻嘉言曰:按诸气膹郁之属于肺者,属于肺之燥也。而古今治气郁之方,用辛香行气,绝无一方治肺之燥者。诸痿喘呕之属于上者,亦属于肺之燥也。而古今治法以痿、呕属阳明,以喘属肺,是则呕与痿属之中下,而惟喘属上矣,所以亦无一方及于肺之燥也。即喘之属于肺者,非表即下,非行气即泻气,间有一二用润剂者,又不得其肯綮。今拟此方名清燥救肺,大约以胃为主,胃土为肺金之母也。其天冬、知母能清金滋水,以苦寒而不用,至如苦寒降火之药,尤在所忌。盖肺金自至于燥,所存阴气,不过一线耳!倘更以苦寒下其气,伤其胃,其人尚有生理乎?诚仿此增损以救肺燥变生诸症,庶克有济耳。
柯韵伯曰:古方用香燥之品以治气郁,不获奏效者,以火就燥也。惟缪仲醇知之,故用甘凉滋润之品,以清金保肺立法。喻氏宗其旨,集诸润剂而制清燥救肺汤,用意深,取药当,无遗蕴矣。石膏、麦冬禀西方之色,多液而甘寒,培肺金主气之源,而气可不郁;土为金母,子病则母虚,用甘草调补中宫生气之源,而金有所恃;金燥则水无以食气而相生,母令子虚矣,取阿胶、胡麻黑色通肾者,滋其阴以上通生水之源,而金始不孤;西方虚,则东实矣,木实金平之,二叶禀东方之色,入通于肝,枇杷叶外应毫毛,固肝家之肺药,而经霜之桑叶,非肺家之肝药乎?损其肺者益其气,人参之甘以补气;气有余便是火,故佐杏仁之苦以降气,气降火亦降,而治节有权,气行则不郁,诸痿喘呕自除矣。要知诸气膹郁,则肺气必大虚。若泥于肺热伤肺之说,而不用人参,必郁不开而火愈炽,皮聚毛落,喘而不休。此名之救肺,凉而能补之谓也。若谓实火可泻,而久服芩、连,反从火化,亡可立待耳!愚所以服膺此方而深赞之。
卷一
当归六黄汤
治阴虚有火,令人盗汗者。
当归 生地 熟地 黄芪 黄芩 黄连 黄柏
水煎服。
季楚重曰:汗本心之液,其出入关乎肝、肺。荣分开合,肝司之;卫分开合,肺司之。顾营卫各有所虚,则各有所汗,阳虚汗责在卫,阴虚汗责在营。然必相须为用,卫气不固于外,由阴气之不藏;营气失守于中,由阳气之不密。故治盗汗之法有二:一由肝血不足,木不生火,而心亦虚,酸枣仁汤补肝即以补心也;一以肝气有余,木反侮金,而肺亦虚,当归六黄汤治肝以治肺也。是方当归之辛养肝血,黄连之苦清肝火,一补一泄,斯为主治;肝火之动,由水虚无以养,生地凉营分之热,熟地补髓中之阴,黄柏苦能坚肾,是泻南补北之义也;肝木之实,由金虚不能制,黄芪益肺中之气,黄芩清肺中之热,是东实西虚之治也。惟阴虚有火,关尺脉旺者始宜。若阴虚无气,津脱液泄,又当以生脉、六味,固阴阳之根。若用芩、连、柏苦寒伤胃,使金水益虚,木火益旺,有措手不及之虞矣。
卷一
苓桂术甘汤
(《金匮》)
治心下有痰饮,胸胁支满,目眩。又曰:短气有微饮,当从小便去之,苓桂术甘汤主之,肾气丸亦主之。肾气丸已见。
茯苓四两 桂枝三两 白术三两 甘草三两
上四味,以水六升,煮取三升,分温三服,小便则利。
赵以德曰:《灵枢》谓心胞络之脉动,则病胸胁支满者,谓痰饮积于心胞,其病则必若是。目眩者,痰饮阻其胸中之阳,不能布水精于上也。茯苓治痰饮,伐肾邪,渗水道,故用以为君;桂枝通阳气,和营卫,开经络,痰水得温则行,故以为臣;白术治风眩,燥痰水,除胀满,故以佐茯苓。然中满者勿食甘,此用甘草何也?盖桂枝之辛,得甘则佐其发散,复益土以制水;且得茯苓则不资满,而反泄满。《本草》曰:甘草能下气,除烦满。故用之也。夫短气有微饮,此水饮停蓄,呼吸不利而然也。《金匮》并出二方,妙义益彰。呼气之短,用苓桂术甘汤之轻清以通其阳,阳化气则小便能出矣;吸气之短,用肾气丸之重降以通其阴,肾气通则关门自利矣。(呼吸二义,发明极精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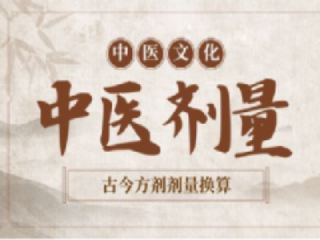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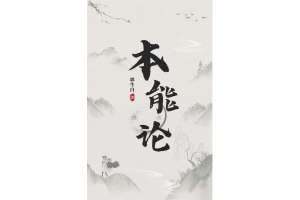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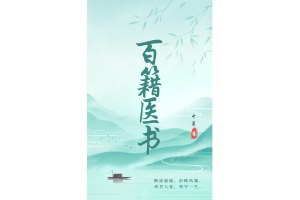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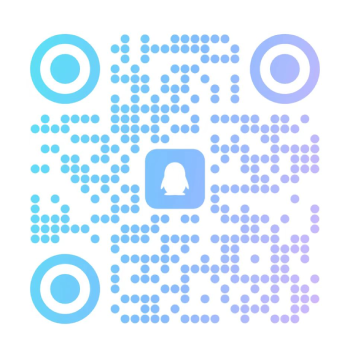
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